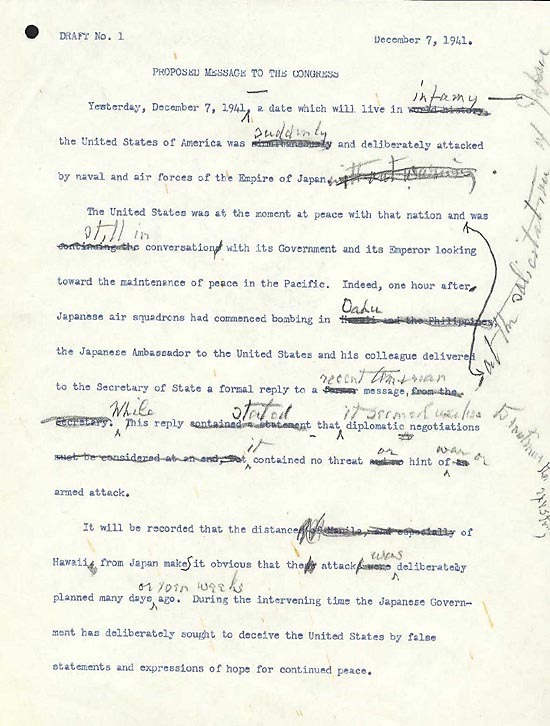论证人类中心主义的逻辑
昨天看到 @大拇哥 在 有哪些有趣、脑洞大开的学术论文? 问题中的回答,介绍了 Bernard Williams 的论文 The Human Prejudice(论文原文可以在这里读,也可以在 2006 年出版的 Philosophy as a Humanistic Discipline 或者 2009 年的一本合集 Peter Singer Under Fire 找到)。文中,Williams 反对 Peter Singer,为 Singer 所反对的物种偏见(speciesism)辩护,认为我们当然应该更关心人的利益,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自己是人。
Williams 论文中有一个被 @大拇哥 详细阐述的内容是 the model of an Ideal or Impartial Observer(理想观察者设定)有多么荒谬。但我想说,这个理想观察者的设定根本不是 Peter Singer 的核心论证。我注意到,Williams 在论文中并没有引用 Singer 关于理想观察者的阐释(我也不知道 Singer 有没有阐释过,至少我读 Animal Liberation 的时候没有印象读到过类似论述,知道出处的朋友可以私信我,谢谢)。Williams 只是说很多功利主义者,包括 Singer,都乐于使用理想观察者设定(Many utilitarians, including Singer, are happy to use the model of an Ideal or Impartial Observer),然后引用了 R. Firth 在 1952 年的一篇论文 Ethical Absolutism and the Ideal Observer 来阐释理想观察者的具体设定。
而我认为 Peter Singer 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理由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形式逻辑的问题,与什么理想观察者设定完全无关。如果我们认同,仅仅因为我们自己是人类,就给予人类优先的地位,那么同样的论证形式,完全可以用来论证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所以如果要论证人类的优先地位,同时又不希望推出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就不能用这样的推理形式。——这才是 Singer 的核心论证。
如果你接受「你属于某个群体,你就应该优先考虑这个群体的利益而不必关心群体之外的其他个体的利益」这样的逻辑,那么这个群体究竟是什么?可以是你的家庭,可以是你所在的班级,可以是你的母校,可以是你的公司,可以是你的祖国,可以是你所在的性别,可以是你所处的智商区间,可以是你所在的种族,也可以是你所在的生物类别,也可以是你所在的星球,甚至还可以是你所在的星系,你所在的某个宇宙……可以是很多东西,那这里面你如何选择?是都可以,还是有些无法接受?选 A 不选 B 的理由又是什么?
有一种区分的理由是,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是因为这些人认为其他种族、其他性别的人类不具有我们同等的智慧(或者说思考能力、表达能力),认为出现歧视的错误是一个事实判断上的错误,而不是价值选择上的错误。Peter Singer,以及我,认为并非如此。歧视,除了误判对方的能力之外,更重要的错误在于「我不关心你的利益」,甚至很多时候「我根本不去思考你还有利益这回事」。
回过头来说,如果你接受类似智慧水平这样的区分理由,你的标准是不是从「我所属的某个群体」变成了「达到某种智慧水平的群体」?那照这个逻辑,智慧爆表甚至无法跟人类在一个层面交流思想的外星人来了,人类是不是就处于劣等地位了?这两种理由(我属于人类所以人类优先,人类最优秀所以人类优先)我认为是不相容的,你只能选其中一个,但不少人类中心主义论者两个理由都在用……
简单写到这里,这个话题显然可以展开很多很多,不可能几段话讲清楚,只是在此提供少许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思路。
–
有兴趣看 Singer 如何反驳的朋友,可以看他的论文 Why Speciesism is Wrong: A Response to Kagan。虽然是 Response to Kagan 但一开头就回应了 Bernard Williams。顺带一说,Kagan 就是耶鲁大学公开课里盘腿坐在讲台上讲死亡哲学的那位 Shelly Kagan /ˈkeɪɡən/。